01
处分的撤销与骚扰的认定
不得不说,处分的撤销,是没有什么悬念的。
武汉大学不可能去推翻法律的判决。
与其质疑武大,我更愿意思考几个法律的问题。
第一个问题是,民事诉讼的“高度盖然性”标准是否应得到体现?
民事诉讼适用的并不是“无罪推定”,而是“高度盖然性标准”。
它体现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零八条:
“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,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,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。”
简单说,在公共场合有没有自慰,是很难百分百判断的,合理的方式,是比较他自慰的可能性,与没有自慰的可能性。
否则,一个人只要有湿疹的证明,就具备了公共场合的自慰权。
第二个问题是,司法中“客观证据”是否应结合“主观感受”?
假设有一种行为,可能出于无知、并无骚扰的意图,也没有“客观证据”,但却让多数女性主观上感到了性骚扰,我们应不应该让这一行为得以避免?
凭常识就知道:当然应该。
对主观感受的考量,可以促进客观行为更加文明。
笔者曾在另一篇文中比较不同国家的法律,详述“主观感受”纳入的必要:
第三个问题是,法律是否应回应观念的变迁?
八年前,柳岩在节目里被开黄腔的时候,全场哄堂大笑,没有多少人觉得不妥。
但放到今天,他们的这些言辞很可能构成性骚扰。
这是因为,公众“观念的水位”不一样了。观念的水位上涨,潜藏的问题自然就会浮起来。过去不被视为问题的问题,开始成为问题。
而法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,需回应社会观念的变迁,需随社会变迁而演进,这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核心特征。
02
论文的争议与学位的保留
笔者曾详细分析过杨景媛的论文:
论文为那些提供过生育价值,又遭遇母职惩罚,从而失去筹码的“黄脸婆”而发声,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了两件事:
第一件事是识别了生育与家庭暴力的因果关系,分析了生育对家庭暴力增加的动态影响。
第二件事是引入了“母职惩罚”这一变量,衡量女性生育后外部选择价值的下降,论证在母职惩罚较高的地区,生育会带来更多的家庭暴力。
这两项研究均为原创与首创。
评价一篇论文是否优秀,应取决于它的内容。包括它的创新性与原创性,它的研究意义与研究途径,它的论证逻辑性与方法合理性,它的结构完整性与语言专业性,它的整体完成度与实践的价值。
作者固然有粗心与疏失,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学术价值。
所幸,武汉大学顶住了舆论的庞大压力,守住了学术的底线。
03
更大的进步仍需时间
这注定是一个让两方都不满意的结果。
一方认定是学术不端,应撤销学位,追究诬告责任;一方认为长时间在公共场合抠裆,怎么可以没有责任,全身而退。
都不满意,体现了撕裂。但撕裂,至少说明有对峙。
而不像曾经那样:一方在桌上大鱼大肉,而做出大鱼大肉的另一方,却上不了桌。
这是一种进步。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。
正如柳岩被开黄腔以前不是问题,但放在现在是个刺眼的问题。
若干年前的杨景媛,遇到抠裆的场景,恐怕也只能不适而愤怒地躲开。
原本温顺的她们忽然变得刺眼了。
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必然遭至更大的反扑。
一边是五千年父权制的沉疴痼疾,一边是刚起步不久的中国女性主义。法律的完善,反骚扰程序的建立,平权意识的提升,基层女性的突围,都仍需时间。
是的,更大的进步仍需时间。
但只要你看,撕裂的舆论场上,更急的是谁?
等得起的,就一定是另一边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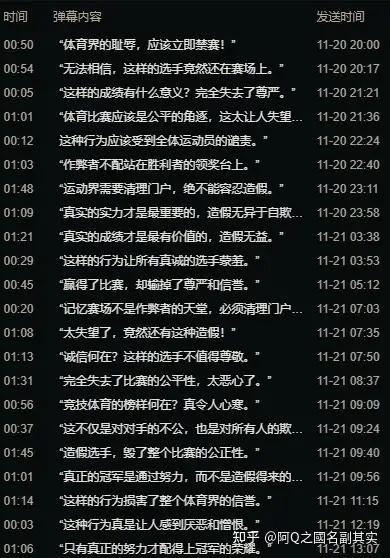


评论0